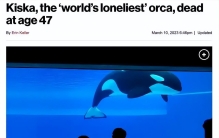我56岁终于明白,手足之情,是这个世界上最暖的依靠
我叫李卫东,今年五十六。
人家都说,五十知天命。可我活到五十六,才觉得自己像个刚睁眼的孩子,懵懵懂懂地,看清了点东西。
年轻的时候,我总觉得,人活着,就得往上奔。
像一根卯足了劲的藤,拼了命地往墙上爬,爬得越高,看得越远,才算没白活。
我做到了。
从一个乡镇工厂的穷小子,到在省城里有自己的公司,有车有房。
儿子争气,国外留学,留在那边,有了体面的工作。
老婆呢,早就过上了她想要的太太生活,每天不是美容就是插花,再不就是跟一群和她一样的太太们喝下午茶,聊些我听不懂也懒得听的奢侈品。
我以为,这就是成功,这就是一个男人该有的样子。
我给家里人撑起了一片天,一片用钱砌起来的,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天。
至于天底下的人,心里暖不暖和,我没空去想。
我觉得,兜里有钱,心里还能不暖和?
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我接到妹妹卫红的那个电话。
那天下午,我刚签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单子,心情不错,正靠在办公室的大班椅上,盘算着年底是不是该把车换了。
手机响了,屏幕上跳着“卫红”两个字。
我有点烦。
妹妹找我,通常没什么好事。
不是她儿子上学差点钱,就是她家里要换个什么大件,再不然,就是老家那边的陈芝麻烂谷子。
我划开接听,语气不算好:“又怎么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是卫红带着哭腔的声音:“哥,你快来吧,大哥……大哥他不行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像是那根玩命往上爬的藤,被人从根上狠狠踹了一脚。
大哥,李卫国。
这个名字在我心里,已经很久没这么清晰地蹦出来过了。
它像一件压在箱子底的旧衣服,你知道它在那儿,但你从来不会想去翻出来看看。
它旧了,过时了,跟你现在这一身光鲜,格格不入。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大哥已经被推进了抢救室。
红色的“抢救中”三个字,像三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眼睛疼。
卫红蹲在墙角,肩膀一抽一抽的,看见我,她站起来,眼睛肿得像两个桃子。
“怎么回事?上个月不还好好的吗?”我问她,声音干得像砂纸。
“脑溢血,突然就倒了。医生说,说让咱们……有个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
多轻飘飘的四个字。
我靠在冰冷的墙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跟大哥,关系算不上好。
甚至可以说,有点疏远。
他是家里的老大,我是老二,卫红是老幺。
从小,他就比我闷,比我犟,也比我……穷。
我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在城里摸爬滚滚,他接了爸的班,在那个半死不活的镇上工厂里,当了一辈子工人。
我发迹了,他还在守着那点死工资,守着我们那座摇摇欲坠的老屋。
我觉得他没出息。
他也觉得我,变了。
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墙。
逢年过节,我也会回去,扔下几千块钱,几条好烟,几瓶好酒,然后坐不到半小时就走。
老屋里那股子潮湿的霉味,大哥身上那股子劣质烟草和汗水混合的味道,都让我觉得窒息。
他总说:“卫东,钱不是那么花的,人不能忘本。”
我听了就烦。
什么叫忘本?我凭自己本事挣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给他钱,让他把老屋修一修,他不肯。
我给他钱,让他换份轻省点的工作,他不肯。
他就像老屋门前那棵老槐树,根扎得死死的,不管外面世界怎么变,他就守在那,一动不动。
我们最后一次吵架,是妈去世的时候。
妈病了很久,一直都是大哥大嫂在跟前伺候。
我呢,就是出钱。
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
我觉得我尽到孝心了。
妈走的那天,我正在外地谈一个重要的合同。
等我签完字,紧赶慢赶地飞回来,妈已经闭上眼了。
灵堂上,大哥一拳打在我脸上。
他眼睛通红,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李卫东,你心里除了钱,还有什么?妈走的时候,最想见的人是你!你知不知道!”
我捂着脸,没还手。
心里却不服气。
我如果不去签那个合同,公司这个月的流水怎么办?几十号员工的工资怎么办?妈后续的丧葬费,天文数字一样的医疗费,从哪来?
难道抱着妈哭,钱就能从天上掉下来吗?
从那以后,我们俩几乎就不说话了。
他没再主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我也一样。
只有卫红,像个夹心饼干,在中间来回传话,维系着那点岌岌可危的联系。
抢救室的门,开了。
医生摘下口罩,一脸疲惫地对我们摇了摇头。
“命是保住了,但是……半身不遂,以后能不能醒过来,不好说。”
我的腿一软,差点跪下去。
卫红已经哭瘫在地上。
大哥被推了出来,躺在病床上,闭着眼,插着各种管子。
他瘦了好多,两颊深陷,头发白了大半。
这还是我那个像山一样结实的大哥吗?
我记忆里的大哥,是那个夏天会带我去河里摸鱼,冬天会把自己的棉手套让给我戴,被人欺负了,会第一个冲上去,用他瘦弱的身体护住我的大哥。
什么时候,他变成眼前这个,需要靠机器维持生命的老头了?
我找了最好的护工,把大哥转到了全省最好的康复医院。
我跟院长拍着胸脯说:“钱不是问题,用最好的药,最好的设备,只要能让他好起来。”
院长客气地跟我握手,说:“李总,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力。”
我以为,我又一次用钱,摆平了所有问题。
可我错了。
钱能买来最好的医疗,却买不来大哥睁开眼睛,再叫我一声“卫东”。
钱能请来最专业的护工,却替代不了亲人在床前的陪伴。
公司的事情,我暂时交给了副总。
我开始每天往医院跑。
起初,我只是在病房里坐一会儿,看看仪器上的数字,问问护工今天的情况,然后就走。
我不知道该跟一个昏迷不醒的人说什么。
我们之间,已经沉默了太多年。
卫红几乎是长在了医院里。
她每天给大哥擦身,按摩,对着他耳朵,絮絮叨叨地讲以前的事。
讲我们小时候,三个人怎么分一个烤红薯。
讲大哥为了给我买一本《水浒传》的小人书,去给人家码头扛了一天麻袋,回来肩膀都磨破了皮。
讲我第一次高考落榜,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是大哥在门外守了一夜,第二天端进来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
这些事,我好多都忘了。
或者说,被我刻意地,埋在了记忆的最深处。
因为这些记忆,都带着一股“穷酸气”,跟我后来的人生,太不搭调。
卫redacted红一边说,一边哭。
我坐在旁边,像个局外人。
心里却像是被什么东西,一下一下地撞着。
有点闷,有点疼。
有一天,卫红有事回家,让我看着大哥。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大哥,还有仪器滴滴答答的声音。
我看着他那张毫无生气的脸,忽然觉得无比陌生。
我们是亲兄弟啊。
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喝着一样的米汤长大的。
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想去摸摸他的脸。
我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我看见了他的手。
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
布满了老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黑泥,皮肤粗糙得像老树皮。
就是这双手,在我小时候,把我高高举过头顶。
就是这双手,在我上大学走的时候,往我手里塞满了煮鸡蛋。
就是这双手,在我创业最难的时候……
等等。
我创业的时候?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我想起一件事。
那是我刚开公司的时候,资金链断了,就差五万块钱,银行的贷款怎么都批不下来。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借钱,求爷爷告奶奶,没一个人肯帮我。
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大哥找到了我。
他从一个旧布包里,掏出五沓用报纸包得整整齐齐的钱。
“卫东,哥没本事,就这点钱,你先拿去用。”
我当时都傻了。
五万块钱,在九十年代末,对一个镇上的工人来说,是天文数字。
我问他哪来的钱。
他支支吾吾,只说是厂里发的奖金,还有这些年攒的。
我信了。
或者说,我那时候太需要那笔钱了,我选择了相信。
我拿着那笔钱,渡过了难关,公司起死回生。
后来,我挣了钱,第一时间就想还给他。
我取了十万,送到他面前。
他却怎么都不要。
他说:“你挣钱不容易,公司刚起步,用钱的地方多。哥不要,你拿着。”
他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过意不去。
从那以后,我每年都给他钱,给他买东西。
我觉得,这是我还他的。
可他好像并不领情。
他总说,我给的,不是他想要的。
现在,看着他那双粗糙的手,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我冲出病房,给卫红打电话。
“卫红,你记不记得,我刚开公司那会儿,大哥给过我五万块钱?”
电话那头,卫红沉默了。
“哥,你……现在才想起来问这个?”
“你快告诉我,那钱到底哪来的?”我几乎是在吼。
卫红叹了口气。
“是爸留下的那套邮票。爸走的时候,跟大哥说,那是咱们家的传家宝,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动。大哥……大哥他给卖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那套邮票,是爸一辈子的心血。
小时候,爸总会戴上白手套,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把那些邮票一张张夹出来,给我们讲上面的故事。
他说,这比金子还贵。
我爸没了以后,大哥就把那本邮册,锁在了他的大木箱子里,谁都不让碰。
我怎么都没想到,他会为了我,把它卖了。
而我,拿着他卖掉“传家宝”换来的钱,挣了更多的钱,然后反过来,用钱去砸他,嫌弃他穷,嫌弃他固执,嫌弃他跟不上我的脚步。
我混蛋!
我真不是个东西!
我冲回病房,跪在床边,握住大哥那只冰冷的手。
“哥……我对不起你……”
我泣不成声。
眼泪落在他的手背上,滚烫。
就在这时,我感觉,他的手指,好像动了一下。
我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他的脸。
他的眼皮,在微微颤动。
我疯了一样地按响了床头的呼叫铃。
医生护士冲了进来。
经过一番检查,医生告诉我,病人有苏醒的迹象,这是个好兆头。
我激动得浑身发抖。
我趴在大哥耳边,不停地跟他说话。
“哥,你听到了吗?我是卫东啊!”
“哥,你快醒醒,你醒过来,我什么都听你的!”
“哥,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去掏鸟窝,我从树上掉下来,把胳膊摔断了,你背着我跑了十几里山路去卫生院,你自己的脚都磨出血了。”
“哥,你还记不记得,我上大学那年,你送我到火车站,火车快开了,你又从窗户里给我塞进来两个热乎乎的烤地瓜,你说,怕哥在路上饿着。”
我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
那些被我丢在脑后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此刻全都涌了上来,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爬到今天的。
在我往上爬的每一步,都有他在下面,用他那双粗糙的手,死死地托着我。
只是我爬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回头看一眼。
快到忘了,那个托着我的人,他也会累,也会老。
大哥终究还是醒了。
但情况很不好。
他不能说话,只有半边身体能动。
眼睛倒是能睁开,但眼神空洞,像个刚出生的婴儿。
医生说,这是脑损伤的后遗症,恢复起来,会非常非常慢。
甚至,有可能一辈子都这样了。
老婆来看过一次,站在病房门口,皱着眉,用丝巾捂着鼻子。
“这什么味儿啊?卫东,你请的什么护工,怎么搞的?”
“你行你来?”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她愣了一下,大概是没见过我用这种语气跟她说话。
“我哪有那个时间。再说,这不是有卫红吗?你出钱就行了,干嘛非得自己在这耗着?公司不要了?”
我看着她那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忽然觉得无比厌烦。
“你走吧。”我说。
“李卫东,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你走。以后,这里的事,你不用管了。”
她气得脸都白了,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地走了。
我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
我把公司,全权委托给了副总。
我把那辆刚开了不到一年的豪车,卖了。
我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
我开始学着,照顾大哥。
这是一件比签下千万合同,难上一万倍的事。
每天,我要给他翻身,拍背,防止他生褥疮。
每隔两个小时,就要重复一次。
他的身体很沉,每次翻身,我都累得满头大汗。
我要给他喂食。
他只能吃流食,要用针管,一点一点地打进鼻饲管里。
快了,怕他呛着。
慢了,一顿饭要喂一个多小时。
我要给他处理大小便。
这是最难的。
我一个大男人,活了五十六年,连我儿子的尿布都没换过。
第一次给他换尿不湿的时候,我差点吐出来。
不是因为脏,也不是因为臭。
而是因为,我看着躺在床上,毫无尊严,任我摆布的大哥,我的心,像被刀子剜一样疼。
这不应该是他。
他应该是那个,能一个人扛起一袋水泥,从一楼上到五楼的李卫国。
他应该是那个,跟我吵架时,嗓门比谁都大的李卫国。
他不应该是这样的。
卫红看我笨手笨脚,总想过来搭把手。
我把她推开了。
“卫红,你回去歇着吧。你也有家,有孩子。这里,有我。”
“哥,你一个人,不行的。”
“行。必须行。”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我欠他的。”
我开始学着跟大哥说话。
尽管他没有任何回应。
我给他读报纸,虽然我知道他可能一个字都听不懂。
我给他讲公司里的事,讲我怎么跟人谈判,怎么签合同。
这些我以前最引以为傲的事,现在讲起来,却觉得索然无味。
讲着讲着,我就讲到了小时候。
“哥,你记不记得咱家院里那棵枣树?每年秋天,你都爬到最高的地方,把最大最红的枣,打下来给我。有一次你脚滑了,从树上摔下来,把腿都磕破了,还把那兜最好的枣,紧紧抱在怀里。”
“哥,你记不记得,妈做的槐花饼?每次妈做好了,你都先让我吃。你说你牙不好,不爱吃甜的。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想让我多吃几口。”
我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把脸埋在他的枕边,像个迷路的孩子。
“哥,你快点好起来,行不行?你再骂我一顿,打我一顿都行。你别这么躺着,我害怕。”
那天晚上,我趴在床边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在摸我的头。
那动作,很轻,很慢,很笨拙。
我猛地惊醒。
是大哥。
他醒着,正看着我。
他那只能动的右手,正放在我的头上。
他的嘴唇在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哥!”
我扑过去,握住他的手。
他的眼睛里,有光。
虽然很微弱,但那是我这几个月来,见过的最亮的光。
他看着我,眼角,滑下一滴泪。
从那天起,大哥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
他能自己吞咽一些半流食了。
他能用那只手,跟我进行简单的交流了。
我指着我自己,问他:“哥,我是谁?”
他会费力地,用手指,在我的手心上,划一个“东”字。
虽然歪歪扭扭,但在我看来,比我签过的任何一个名字都好看。
康复治疗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
每天,康-复师会来,像掰木偶一样,活动他僵硬的关节。
大哥疼得满脸是汗,浑身发抖,但他一声不吭。
我看着心疼,跟医生说,能不能轻点。
医生说:“李先生,康复就是个跟自己较劲的过程。他越疼,说明他的神经越有反应,这是好事。”
我懂。
我只是,看不了他受苦。
我开始推着轮椅,带他去医院的小花园里晒太阳。
秋天的阳光,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很舒服。
我指着天上的云,地上的草,飞过的鸟,一样一样地告诉他。
“哥,你看,那朵云,像不像你以前给我买的棉花糖?”
“哥,你看那只鸟,它叫得真好听,等你好利索了,我带你去山里,听真正的鸟叫。”
他会微微地点头,或者眨眨眼,表示他听到了。
有一次,花园里有个小孩子,在吹泡泡。
五颜六色的泡泡,在阳光下,飘飘悠悠。
大哥的眼睛,一直追着那些泡泡。
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孩子般的好奇和向往。
我心里一动。
第二天,我买了好几瓶泡泡水。
在花园里,我学着那个孩子的样子,给他吹泡泡。
一个又一个的泡泡,从我面前飞起来,飞向他。
有的落在他身上,有的落在他脸上,然后“啪”的一声,碎了,留下一小片水渍。
他笑了。
虽然只是嘴角,极其轻微地,向上扯了一下。
但我看清了。
他笑了。
我激动得,像个得了满分的孩子,差点跳起来。
“哥,你笑了!你笑了!”
我一边吹,一边笑,笑着笑着,眼泪又下来了。
我五十六岁了。
在商场上,我是说一不二的李总。
在家里,我是高高在上的大家长。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为了让一个人笑,像个傻子一样,在医院的花园里,吹一下午的泡泡。
而这个人,是我的大哥。
那个下午,阳光很好。
泡泡碎掉的声音,和我自己的心跳声,交织在一起。
我忽然觉得,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一笔“生意”。
这笔生意,不赚钱。
甚至,一直在亏钱。
但我得到的,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东西。
儿子的电话,是在一个周末打来的。
他知道了家里的事,很担心。
“爸,要不我回来吧?”
“不用。”我对着电话说,“你好好工作,家里有我。”
“可是……”
“别可是了。”我打断他,“你以前,听过我给你讲你大伯的事吗?”
电话那头,儿子沉默了。
是啊,我从来没讲过。
我总觉得,大哥的人生,是失败的,是灰暗的,不值得拿来教育我那个前途光明的儿子。
“你大伯,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我对着电话,第一次,用一种平静而骄傲的语气,讲起了大哥。
我讲他怎么卖掉邮票,让我渡过难关。
我讲他怎么一辈子勤勤恳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们。
我讲他怎么像一棵树,牢牢地扎在老家的土地上,守护着我们这个家,最后的根。
我讲了很久。
电话那头,儿子一直在安静地听。
最后,他说:“爸,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会努力工作。以后,我跟你一起,养大伯。”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
夕阳正把天空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色。
我忽然觉得,我那个远在天边的儿子,跟我,近了很多。
大哥的康复,进入了平台期。
他能自己坐起来了,也能在我的搀扶下,勉强站一会儿。
但语言功能,一直没有恢复。
医生建议,可以回家休养,熟悉的环境,对病人情绪有好处。
我跟卫红商量,把大哥接回了老屋。
那座我嫌弃了半辈子的老屋。
再次踏进去,我却没有了以前那种窒息感。
屋子被卫红收拾得很干净。
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下遒劲的枝干,指向天空。
我把大哥的房间,安排在朝阳的那一间。
我买了新的床,新的被褥。
墙上,我挂了一幅放大的照片。
那是我们兄妹三个人,唯一的一张合影。
照片上,大哥十几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咧着嘴笑,露出两颗虎牙。
我七八岁,躲在他身后,只露了半个脑袋。
卫红还是个小不点,被大哥抱在怀里,手里拿着一根冰棍。
照片已经泛黄了。
但上面的笑容,却那么清晰。
我把大哥安顿好,开始学着,过一种我从未有过的生活。
我学着生炉子。
第一次,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呛得我直流眼泪。
我学着做饭。
我打电话问卫红,大哥以前最爱吃什么。
卫红说,大哥不挑食,但最爱吃手擀面,配上西红柿鸡蛋的卤子。
我从和面开始学。
面和硬了,擀不动。
和软了,粘一手。
切出来的面条,有的像筷子,有的像皮带。
第一碗面,煮出来,成了一锅面糊糊。
我端到大哥面前,自己都没脸看。
大哥却看着那碗面,眼睛亮亮的。
他用那只还算灵便的手,颤颤巍巍地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费力地,往嘴里送。
他吃得很慢,很吃力。
但,他把一整碗,都吃完了。
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然后,他看着我,咧开嘴,又笑了。
那一天,我守着炉子,给他做了一整天的手擀面。
我的手艺,越来越好。
面条,也越来越筋道。
我发现,给家人做饭,看着他们吃下去,那种满足感,比签下一个亿的合同,还要强烈。
日子,就在这生火、做饭、洗衣、康复的循环中,一天天过去。
很慢,很平淡。
甚至,有点枯燥。
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不再失眠了。
也不再需要靠昂贵的茶叶和雪茄来提神了。
每天晚上,我给大哥洗完脚,把他安顿睡下,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我自己,也很快就能睡着。
睡得特别香。
有时候,我会梦到小时候。
梦到夏天傍晚,我们三个人,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听奶奶讲故事。
奶奶摇着蒲扇,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你们看,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亲人。人死了,就变成星星,在天上看着你们呢。”
“那我们要是想他们了,怎么办?”我问。
奶奶说:“那你们就看看天。看到最亮的那颗,就是他。”
冬去春来。
老屋院子里的那棵槐树,又发出了新芽。
大哥的身体,也在一点点地好转。
他已经能拄着拐杖,自己走一小段路了。
虽然走得很慢,像一只笨拙的企鹅。
但他毕竟,能自己走了。
有一天,我扶着他在院子里散步。
卫红来了,提着一篮子自己家种的青菜。
我们三个人,就坐在院子里的老藤椅上,晒着太阳。
谁也没说话。
只有风吹过槐树叶子,沙沙作响。
大哥忽然,抬起手,指了指我,又指了指卫红。
然后,他张开嘴,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发出了两个,含糊不清的音节。
“家……”
“……人。”
我和卫红,都愣住了。
然后,我们俩,抱在一起,哭得像两个孩子。
大哥看着我们,浑浊的眼睛里,也噙满了泪。
他伸出那只布满老茧的手,一只,搭在我的肩膀上。
一只,搭在卫红的肩膀上。
然后,用力地,把我们往他身边,拢了拢。
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三个人,又变回了多年前那张黑白照片里的样子。
紧紧地,靠在一起。
我今年五十六岁。
我没有了豪车,住着租来的房子。
我的公司,效益大不如前。
我的老婆,跟我提出了离婚。
我那个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成功人士的光环,已经褪得差不多了。
按我以前的标准,我现在,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但是。
我每天,都能吃到热乎乎的饭菜。
我每天,都能看到大哥的笑脸。
我每天,都能跟妹妹,聊聊家常。
我扶着大哥,在院子里,种下了几棵西红柿。
我看着它们,从一棵小苗,慢慢长大,开花,结果。
我忽然明白,我以前拼了命往上爬,以为爬得越高,风景越好。
可我忘了,风景再好,也是给别人看的。
真正能支撑你,让你觉得温暖的,不是你站在多高的地方,而是你的根,扎在多深的地方。
手足之情,就是我们人生的根。
它平时,藏在土里,你看不见它。
你甚至会觉得,它碍事,它拖累了你向上生长。
可当风雨来临,当你要被连根拔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是那些你看不见的根,在拼了命地,抓着土地,给你支撑,给你力量。
让你不至于,倒下去。
我五十六岁,才明白这个道理。
不算太晚。
因为我一回头,我的哥哥,我的妹妹,他们都还在。
这就够了。
这就比我前半辈子挣的所有钱,加起来,都更让我觉得,富有。
那天下午,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我给大哥削了一个苹果,用小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就像小时候,他喂我吃东西那样,一块一块地,喂到他嘴里。
他吃得很慢,但吃得很香。
卫红坐在一旁,织着毛衣,嘴里哼着我们小时候的歌谣。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我看着他们,心里忽然就觉得,特别的安宁。
这,就是家吧。
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暖的依靠。
大家都在看
-
稀客到访!“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鳽首次现身清新 近日,清新迎来一名“稀客”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鳽现身笔架山。这是清新首次发现海南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鳽现身清新。林业部门 供图2月7日晚11时35分,清新一名生态摄像爱好者余力涛在笔架山蹲点拍摄 ... 世界之最02-11
-
近4万根毫米级钢丝拉起世界第一高桥(探访全球第一) 截至1月28日,“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贵州花江峡谷大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30万人次,通行车辆超20万辆次,持续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大桥带来的发展溢出效应令人瞩目,而深入大桥肌理探查,你会发现,支撑起这座庞然 ... 世界之最02-11
-
大石桥,到底骗了多少人?居然拥有5个“世界之最”! 大石桥到底有什么魅力?别被那些“世界之最”段子糊弄了,真正值得你去的,是那股平实打拼的劲头和背后那一片生机盎然的产业天地。你知道吗,镁产业正跑得飞快,不只是满足耐火材料的需求,更朝着低碳、智能、绿色的 ... 世界之最02-09
-
“我眼里的妈妈是世界上最疼我的人”,这些妈妈们的故事真暖! 以情润童心 用爱伴成长——2025年全国妇联推动爱心妈妈关爱服务工作精准化规范化机制化得知留守女童欣欣的“微心愿”是看大海,山东泗水的“微爱妈妈”颜颖将这个愿望放在了心上。趁着暑假,她立刻带欣欣奔赴日照, ... 世界之最02-07
-
那些离谱的世界之最:你知道吗?带你领略地球上的“怪奇”奇观 嘿,朋友们!今天咱们不聊平凡,不讲常识,而是带你走进那些令人惊掉下巴、离谱到极点的“世界之最”。你知道吗?地球上竟然藏着一些你从未听说过的超级奇迹——有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大,有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小,有的甚 ... 世界之最02-06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宣传片首次落地世界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 当地时间2月3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宣传片在阿根廷乌斯怀亚市中心户外两块大型电子屏幕滚动播出。这是总台春晚宣传片首次在被誉为“世界最南端城市”的乌斯怀亚亮相,标志着总台春节文化国际传播迈出新的 ... 世界之最02-05
-
兴化,到底骗了多少人?居然拥有5个“世界之最”! 兴化,众人熟知的“里下河水乡”,其实一直躲在江苏的角落里,默默散发着属于自己的魅力。曾有人说“世界之最”不过是噱头,但这里那片连绵的垛田、花海、那水网交错的古镇和人文故事,却是真实且动人的存在。近年来 ... 世界之最02-05
-
中东最另类的国家——阿曼,阿拉伯世界最"安静"最没存在感 看中东新闻,永远是沙漠石油、战乱爆炸,伊拉克伊朗天天刷屏,感觉那些地方除了打仗啥也没有。和伊拉克的经常打仗、伊朗的浑身是刺、叙利亚的混乱不堪相比,阿曼给人的印象没那么深,在中东这片战乱的地方,阿曼这个 ... 世界之最02-04
-
3106件艺术品!墨西哥刺绣纺织品展规模创世界之最 近日,墨西哥举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刺绣纺织品展览,汇集全国32个州200位工匠创作的3106件艺术品,成功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颁奖仪式上,墨西哥旅游部长约瑟芬娜·罗德里格斯(Josefina Rodríguez)表示:“墨 ... 世界之最02-04
-
“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而我还在叛逆期” “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 这是作家张洁的体验,她把这种“苦”的花样百出变成了一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多年之后,张洁也走了,留下她“无字”的人生, ... 世界之最02-03
相关文章
- 联合国官员:苏丹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 “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而我还在叛逆期”
- 经济学家马光远:黄金是世界上最烂的投资,预测金价就是算命
- 关于俄罗斯的13条世界之最
- 世界最中心!麦迪逊广场最高分:甜瓜62一枝独秀 科比61乔詹随后
- 世界上最脏的病是什么病?不是艾滋,最脏的是这3种疾病
- 狗剩:C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球员之一;瓜帅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 邵武,到底骗了多少人?居然拥有 5 个 “世界之最”!
- 世界上最顽固的病是什么病?困扰排名前3的疾病,经历过的太能扛
- 世界上打仗最狠的五个国家,美国并未在其中,中国排名如何?
- 心软是病,情深致命!成年世界最残忍的5条生存法则,你懂了几个
- 山东济南,到底骗了多少人?居然拥有 5 个 “世界之最”!
- 戈登:欧冠是世界最顶级的赛事,我认为它能激发出球员的额外潜能
- 世界上最古老的10个文明
- 芬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真实的芬兰:人民很压抑,物质不丰富
- 江苏无锡,到底骗了多少人?居然拥有 5 个 “世界之最”!
- 俄罗斯的世界自然遗产
- 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在哪里?连鱼都无法存活,到底有多可怕?
- 世界上最长寿的十个国家和地区:
- 世界最奇葩国家,花费巨资买了400万领土,现在国家成了超级大国
热门阅读
-
世界最恐怖的3个地方,第一名位于中国,你去过吗? 01-04
-
世界上最长寿的人前10排行榜,中国占6个! 02-14
-
盘点一下世界之最,最长丁丁竟然有60㎝!! 04-26
-
全球最值钱的五大货币,竟然没有人民币和美元 05-10
-
莉娜·安德森 - 世界上最美丽的成人模特 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