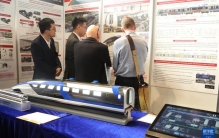秦始皇被骂暴君可他在位的十一年做的改革足以改变一个朝代的命运
是的,后人皆言秦始皇是暴君,可他以皇帝之名在位的短短十一年,所推行的雷霆改革,其雄心与魄力,足以扭转一个朝代的命运,甚至重塑华夏的筋骨。这究竟是夸大其词的辩解,还是被尘封的历史真相?
韩非子解老有言:“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然则,若有一人,欲以雷霆万钧之力,毕其功于一役,将天下之难事、大事,在短短十一年间尽数完成,其行径在时人眼中,与“暴”何异?这其中的功过是非,或许并非史书上那寥寥数笔的“焚书坑儒”、“严刑峻法”所能概括。
欲知其人,必先观其世。当六国狼烟散尽,一个名为“秦”的庞然大物矗立于东方,天下初定,人心未安。在那些被征服的土地上,亡国之民的眼中,咸阳宫中的那位始皇帝,是家国破碎的罪魁,是践踏祖宗基业的仇雠。他们口中的“暴”,是切肤之痛,是血泪之仇,真实得容不得半分辩驳。
然而,真相往往隐匿于表象之下。正如深海的洋流,表面看似波澜不惊,其下却涌动着足以改变大陆格局的磅礴伟力。始皇帝在位的十一年,便是这样一股暗流。他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铸就万世不拔之基业,还是藏着一个更宏大、更不为人知的秘密?或许,只有真正深入那段尘封的岁月,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才能窥见那“暴政”表象之下,所掩盖的惊天图谋。

01
北朔郡的风,像是裹着沙砾的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我叫芦知远,曾是赵国邯郸城里一个颇有些名气的儒生。我的祖父,曾在赵王面前讲经,我的父亲,也曾是受人敬重的学官。
而我,如今只是这北朔郡边城里一个苟延残喘的教书先生,守着几卷残破的竹简,教着三五个衣衫褴褛的孩童,念着早已被咸阳朝廷废止的赵国文字。
这是一种无声的对抗,也是一种绝望的坚守。
每当教孩子们写下“赵”字那熟悉的笔画时,我胸中都会涌起一阵酸楚。国已破,家已亡,连这承载着先祖记忆的文字,都成了罪证。
秦王政,不,如今是始皇帝了。他用铁蹄踏碎了六国的山河,也踏碎了我们这些读书人最后的尊严。
天下人都骂他是暴君,我更是对他恨之入骨。若非他,我本该在邯郸的学宫里,与同道好友饮酒论道,而不是在这鸟不拉屎的边郡,与沙土为伴。
那天,风沙格外的大,昏黄的天地间,连人的影子都变得模糊。我正教着孩子们背诵诗经中的黍离,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悲凉,让我一时失神。
就在这时,一阵沉重而整齐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大地震动,仿佛有千军万马正在开来。
孩子们吓得躲在我身后,瑟瑟发抖。我强作镇定,走出破败的草屋,眯着眼望向风沙的来处。
只见一队队身着黑甲的秦军,如同一道黑色的铁流,涌入了我们这个破落的村庄。他们面无表情,眼神冷酷,手中的戈矛闪烁着森然的寒光。
为首的是一名官员,身着绣着繁复纹路的官服,头戴高冠,嘴唇抿成一条刻薄的线。他骑在马上,居高临下地扫视着我们这些蜷缩在屋檐下的亡国之民,眼神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轻蔑。
村民们吓得跪倒在地,连头都不敢抬。我却直挺挺地站着,胸中的恨意压过了恐惧。
那官员的目光最终落在了我身上,或许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还站着。
他身边的护卫策马上前,用戈矛的末端指着我,厉声喝道:“大胆刁民,见上官为何不跪?”
我冷笑一声,没有说话。跪?我芦家的膝盖,上跪天地君亲师,下跪祖宗先贤,何时跪过虎狼之辈?
那官员似乎对我这副“臭脾气”有些意外,他挥了挥手,制止了护卫的呵斥。他翻身下马,缓缓向我走来。
“你就是芦知远?”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我心中一惊,他竟知道我的名字?
“是又如何?”我昂着头,直视着他。
他从袖中取出一卷帛书,在我面前展开。“奉陛下诏令,”他一字一顿地念道,“征召原六国方士、儒生、百工技艺之士,即刻启程,往朔方大营,听候调遣。凡有不从者,以叛逆论处,斩!”
“斩”字出口,寒气逼人。
我身后的村民们发出一阵压抑的惊呼。
我的心,则瞬间沉入了谷底。
朔方大营,那是修筑长城的地方!征召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去做什么?去和泥,去搬砖,去当那些被活活累死的民夫的替死鬼?
这是要把我们这些六国旧人往死路上逼啊!
“暴君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我咬着牙,从牙缝里迸出这句话。
那官员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身后的甲士“唰”地一声拔出了腰间的青铜剑,剑锋直指我的咽喉。
“你敢辱骂陛下?”
我闭上眼睛,昂起头,准备引颈就戮。死在这些秦狗的剑下,总好过去长城工地上被活活折磨死。
然而,预想中的疼痛并未传来。
我睁开眼,却见那官员抬手拦住了甲士。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愤怒,反而多了一丝奇异的光。
“你的胆子,比你的学问要大。”他收起帛书,淡淡地说道,“收拾一下,跟我走吧。”
他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紧接着,他补充了一句更让我匪夷所思的话。
“芦知远,陛下专门提到了你的名字。”他盯着我的眼睛,缓缓说道,“他要用的,不是你的手,是你的脑子。”

02
我的脑子?一个亡国儒生的脑子,对那位高高在上的始皇帝,能有什么用处?
我满心疑窦,却身不由己。在秦军的“护送”下,我与其他被征召来的儒生、工匠一起,被押送着离开了家园。队伍绵延数里,一路之上,哭声、咒骂声不绝于耳。
所有人都认定,我们此去,必死无疑。
然而,队伍前进的方向,却并非是传说中那座用血肉堆砌的长城。我们一路向西,穿过荒芜的戈壁,最终抵达了一处巨大的盆地。
盆地之中,旌旗林立,营帐如云,数以万计的民夫和士兵聚集于此,却并非在修筑城墙,而是在修路。
那是一条我从未见过的路。
它笔直得像一根拉紧的琴弦,从盆地的一端,刺向另一端,仿佛要将整个大地劈开。它的宽度,足以容纳十余辆马车并行。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它的建造方式。
工人们用巨大的夯锤,将混杂着砂石、黏土的“三合土”一层层地夯实,每一层的厚度,都有专门的官员用标尺严格测量。路基之深,路面之平整,远超我所见过的任何一条驰道。
这简直不像是在修路,更像是在建造一座横卧于大地的城墙。
负责管理我们这些新来者的,是那位将我带来的高冠官员。我后来才知道,他名叫冯阶,是丞相李斯的得意门生,深得始皇帝信任。
冯阶将我们这批读书人单独分了出来,并没有让我们去干那些搬石夯土的粗活。他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文具:秦国的小篆刻刀、空白的竹简,以及一本厚厚的、用以对照学习的仓颉篇。
我们的任务,是整理和记录。记录每天工程的进度、物料的消耗、人力的调配。所有的数据,都必须用统一的秦国小篆,统一的度量衡单位来记录。
我捏着那柄冰冷的刻刀,看着眼前陌生的秦篆,心中百感交集。曾几何,我以能书写一手漂亮的赵国大篆而自傲,如今却要被迫使用这“仇人”的文字。
这不仅仅是书写方式的改变,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阉割。
起初,我怀着满腔的愤懑,消极怠工。我故意将“石”与“石”旁的“担”混淆,将长度单位“步”与“引”的数据弄错,试图用这种微不足道的方式,来拖延工程的进度。
然而,冯阶似乎早就料到了我们的心思。他不定时地抽查我们的记录,一旦发现错误,惩罚极其严厉。轻则鞭笞,重则直接拖出去斩首。
几天之内,就有两名心怀故国的楚地儒生因为“记录不力”而被当众处死。鲜血染红了黄土,也浇灭了我心中那点可笑的对抗之火。
我开始老老实实地工作,但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深。
始皇帝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在这荒无人烟的北地,修建这样一条“通天大道”,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他的巡狩仪仗走得更平稳一些?
这条路,笔直地指向西方,路的尽头,是茫茫的、未知的世界。
我结识了一位来自鲁地的老工匠,姓公输,据说还是那位巧匠公输班的后人。他负责整个工程的技术指导,对这条路倾注了近乎疯魔的热情。
一日,我向他请教,为何这路要修得如此笔直宽阔。
老公输抚摸着一段刚刚夯实的路面,眼神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他压低声音对我说:“芦先生,你以为这只是路吗?不,这不是路,这是帝国的经脉!血脉通达,帝国才能如臂使指。陛下的雄心,是要让帝国的政令,从咸阳发出,十日之内,便能抵达最遥远的边疆!”
十日之内,抵达边疆?
我被他的话震惊了。在这个靠车马脚力的时代,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看着眼前这条无限延伸的“直道”,我又觉得,这似乎并非不可能。
我开始对这个庞大的工程产生了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憎恨,有畏惧,但更多的是一种源于学者本能的好奇。
我不再满足于简单地记录数字,而是开始偷偷地将所有的数据抄录下来,试图从这些枯燥的数字中,拼凑出整个工程的全貌,揣测始皇帝的真实意图。
这天夜里,我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溜进了存放工程图纸的中央营帐。冯阶今晚被紧急召走,帐内只有一个昏昏欲睡的守卫。
我小心翼翼地绕过他,来到那只巨大的木箱前。箱子没有上锁。
我屏住呼吸,打开了箱盖。里面全是绘制在羊皮上的图纸,详细地标注着路线、地形、以及各种我不懂的符号。
我翻找着,希望能找到一张总览图。
就在箱子的最底层,我摸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东西。那不是坚硬的竹简或柔软的羊皮,而是一卷光滑的丝帛。
我心中一动,悄悄地将它取出,藏入袖中,然后迅速离开了营帐。
回到我那简陋的铺位上,我借着微弱的月光,缓缓展开了那卷丝帛。
只看了一眼,我的呼吸便瞬间停止了。
那是一幅大秦帝国的全舆图。山川、河流、郡县,无不详尽。图上,一道道红色的线条纵横交错,将整个帝国连接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些红线,正是我眼前正在修建的这种“直道”。
然而,真正让我通体冰凉的,是图的东方。
一条粗大的红色箭头,从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越过海岸,直指茫茫大海深处的一个小点。
那个小点的旁边,用朱砂写着两个让我头皮发麻的字蓬莱。
原来如此!
我瞬间全明白了。
什么帝国的经脉,什么十日抵达边疆,全都是骗人的鬼话!
耗费万民之力,驅使百万之众,流尽血汗,牺牲无数生命,修建这通天彻地的庞大工程,归根结底,竟然只是为了那个暴君能够更方便地去寻找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药!
一股巨大的荒谬感和愤怒,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
我死死地攥着那卷丝帛,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
这个自私、疯狂的暴君!为了他一个人的妄想,竟然要让整个天下为之陪葬!

03
对始皇帝的恨意,在那一刻达到了顶点。
这张通往“蓬莱”的地图,像一根毒刺,扎进了我的心里。它将我之前对这个庞大工程产生的所有好奇与敬畏,全都转化为了深刻的鄙夷与愤怒。
我不能容忍,无数人的血汗,乃至生命,都为一个人的虚妄幻想而白白牺牲。
我必须做点什么。
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儒生。但,我还有我的脑子。冯阶不是说,始皇帝看重的是我的脑子吗?那我就用我的脑子,来给这个疯狂的工程,制造一点小小的“麻烦”。
从那天起,我工作的态度变得前所未有的“认真”。
我不再消极怠工,而是主动承担了更多的记录任务。我利用自己深厚的经学和算学功底,很快就赢得了那些秦吏的信任。他们开始将更核心的后勤调度与人力分配的统计工作交给我。
机会来了。
我开始利用他们对我这个“外行”的轻视,在记录中做手脚。我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篡改,那太容易被发现。我做的,是利用不同历法之间的微小差异。
秦国使用颛顼历,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而我精通早已被废弃的古赵国历法,其在闰月的设置上,与颛顼历有着极其细微但会随时间累积的偏差。
我开始在我负责的物料需求和工期推算的竹简上,不动声色地引入这种偏差。也许一天两天看不出什么,但十天,一个月,甚至一个季度之后,这种微小的错误就会被无限放大。到时候,前线工地的物料会供应不上,人力调度会陷入混乱,整个工程的进度,必将因此而大大延缓。
这是我一个儒生,所能做出的最决绝的反抗。
我沉浸在这种秘密的报复所带来的快感之中,每天看着那些秦吏对我记录的精准赞不绝口,心中便涌起一阵阵冰冷的快意。
然而,我还是低估了秦国这个庞大机器的精密程度。
半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自己的案前“奋笔疾书”,营帐的帘子突然被掀开,两个人走了进来。
一个是冯阶,另一个,则是一个陌生的中年人。
这人看上去四十多岁,身材清瘦,穿着一身普通的麻布衣服,就像个老农。但他的眼睛,却异常明亮,仿佛能看穿人心。他身上有一种与这尘土飞扬的工地格格不入的儒雅与沉静。
我心中“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冯阶的面色很不好看,他指着我,对那中年人说:“公输先生,就是他。”
公输先生?难道他就是那位传说中的总工程师,公输班的后人,公输磐?
公输磐没有看我,而是径直走到我的案前,拿起我刚刚刻写好的一卷竹简,又从自己的袖中,取出了另一卷。
他将两卷竹简并排摊开,沉默地看了许久。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我看到,他手中的那卷竹简上,用红色的笔迹,圈出了好几处我做的手脚。
他发现了!
我攥紧了拳头,额头上渗出了冷汗。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就是一死。
然而,公输磐的反应再次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下令将我抓起来,也没有厉声质问,只是抬起头,用那双明亮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
“你的算学很好。”他开口了,声音很温和,“能想到用古历法的时差来制造混乱,非大才不能为也。”
我愣住了。他这是在夸我?
“只可惜,”他话锋一转,“用错了地方。”
冯阶在旁边冷哼一声:“公输先生,此等乱臣贼子,何必与他多言,直接按律处置便是!”
公输磐却摇了摇头,他对冯阶说:“冯大人,此事交给我来处理,可否?”
冯阶似乎对公输磐十分敬重,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冷着脸退出了营帐。
帐内只剩下我和公输磐两个人。
他没有审问我,而是将那两卷竹简收起,对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芦先生,可否随我走一趟?”
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事已至此,我别无选择。我跟着他走出了营帐,来到工地旁的一座高高的瞭望台上。
站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盆地的景象。那条笔直的“天路”如同一条黑色的巨龙,匍匐在大地上,无数渺小的人影在它身上忙碌着,像蝼蚁一般。
“芦先生觉得,此等工程,如何?”公输磐指着下方,问道。
“劳民伤财,荼毒天下。”我毫不客气地答道。
公输磐笑了笑,不以为忤。“那先生可知,为何要如此劳民伤财?”
我冷笑一声,想起了那张“蓬莱”地图,讥讽道:“不就是为了满足陛下一人求仙问道的私欲吗?修一条通天大道,好让他驾着马车去海上寻那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山!”
我说完,准备迎接他的怒火。
可公输磐的脸上,却露出了极其古怪的神情,那是一种混合了惊讶、错愕,甚至是一丝怜悯的表情。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求仙问道”他喃喃自语,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原来在你们眼中,陛下所做的一切,就只是为了这个?”
他转过身,一双眼睛灼灼地盯着我,那目光深邃得仿佛能将人的灵魂吸进去。
“芦知远,你以为你看到了真相,但你看到的,不过是陛下想让天下人看到的表象罢了。”
他从怀中,缓缓掏出另一卷用明黄色丝线捆绑的图卷,上面烙着一个清晰的“御览”印章。
“你看到了通往东海的蓬莱路,那不过是个幌子。”公输磐的声音压得极低,却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这条直道真正的方向,是西边!是那些连匈奴都未曾踏足的,更遥远的西域!”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西域?
“陛下常说,六王毕,四海一,但这天下,真的一了吗?文字不同,车轨各异,度量不一,人心更是千差万别。这样的一,不过是浮沙之上建高塔,风一吹,就散了。”
公输磐的声音带着一种莫名的激动,“所以,陛下要做的,不是征服,而是重塑!他要将这天下,炼成一块铁板!这直道,是骨架;统一的文字、车轨、度量衡,是血肉。但这些,都还不够!”
他解开那卷御览图卷的丝线,在我面前,缓缓展开。
“你以为,陛下穷尽天下之力,只是为了修路,只是为了寻找长生?”
公输磐指着图卷,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你错了!大错特错!始皇帝的雄心,远非尔等所能想象!他要征服的,从来不是什么土地,也不是什么敌人。他要征服的,是比时间和空间更可怕的东西!”

我死死地盯着他展开的那卷丝帛,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那上面画的,根本不是什么地图。
那是一副无比繁复、无比精密的图样,由无数我从未见过的符号、线条和几何图形构成。它既像是一副描绘星辰轨迹的星象图,但其上的星宿排列却完全违背了我所知的任何一种天文学说;它又像是一张某种机械的构造图,但那结构之复杂,原理之诡异,完全超出了人类工艺的极限。
图样的正中央,是一个代表着“中宫”的符号,而那个符号的形状,赫然便是秦国玉玺上的“皇”字。无数的线条从这个“皇”字延伸出去,连接着图上那些怪异的星辰与机械构件,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巨大法阵,或者说一个系统。
我的喉咙一阵发干,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这一刻凝固了。
“焚书,不是为了愚民,是为了清扫出足够干净的地基。”公输磐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如同梦呓,却又清晰得可怕,“坑儒,也不是为了泄愤,是为了剔除那些阻碍系统运转的杂音。至于这修直道,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芦知远,你还不明白吗?”
“这些,都不是目的,这些都只是工具!是用来构建一个前所未闻的庞大机器的零件和燃料!”他的手指,重重地落在了图样中央那个“皇”字之上。
“史书会唾骂他,后人会憎恨他,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建造过程中的烈火、浓烟与撕心裂肺的哀嚎。他们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却永远看不到,那烈火之中,究竟在锻造着什么!”
公输磐抬起头,目光越过我,望向遥远的咸阳方向,眼神中充满了狂热的崇拜与深深的恐惧。
“陛下他他不是在建立一个属人的王朝。他在建造一台足以撼动天地的巨型机器。而我们所有人,你,我,冯大人,天下万民,都只是这台机器上的一枚齿轮,一根铆钉。这些你眼中的暴政,这些所谓的改革,它们改变的,将不仅仅是一个朝代的命运。”
我呆呆地看着那张图,大脑一片轰鸣。图上的那些符号仿佛活了过来,在我眼前旋转、跳跃、组合,隐隐指向一个我完全无法理解,却又感到无比恐惧的终极目的。
那是一种,足以颠覆整个世界认知的、绝对的疯狂。
04
我颤抖着,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触及神明领域后的巨大战栗。这张图,就是始皇帝藏在雷霆暴政之下,那个最深、最黑暗的秘密。
公输磐收起了图卷,仿佛那是什么会灼伤凡人魂魄的禁忌之物。
“现在,你还觉得,这是为了求长生吗?”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悲悯,“长生?陛下若只求一己之长生,何须如此大费周章。他要的,是这个名为秦的帝国,长生不死!”
“帝国长生”我喃喃自语,这四个字比任何神话都更加疯狂。
“自古以来,王朝更迭,如四时轮转,夏、商、周,无一例外。在儒生眼中,这是天道循环,是德行有亏,天命转移。”公输磐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但在陛下眼中,这是病!是天地间最大的顽疾!”
“他认为,所谓的天命,不过是一种规律。既然是规律,就可以被观测,被计算,甚至被改写!”
我的儒学信仰在这一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将天命视为一种可以改写的规律?这是何等的狂妄与亵渎!
“这不可能!天道在上,岂是人力可以妄为!”我激动地反驳。
“人力?”公输磐笑了,那笑容里满是苦涩,“寻常人力自然不行。但若是以整个天下为熔炉,以万民为薪炭,以法度为铁锤,以郡县直道为脉络,以统一的文字思想为灵魂,锻造出一台前所未有的人道机器呢?”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仿佛怕被冥冥中的什么东西听到。
“焚书,是为了抹去历史的惯性。天下人只记得周亡于秦,却忘了周也曾代商,商也曾代夏。这些记忆,就是王朝更迭的种子,是天命的低语。陛下要做的,是让天下人的思想,从一张白纸开始,在这张白纸上,只允许写一个秦字。”
“坑儒,是为了剪除解读天命的人。天降灾异,河水倒流,在你们看来,是上天示警。但在陛下的机器里,这只是一个需要被修复的故障。而你们这些儒生,就是利用故障来煽动人心的病毒。所以,必须清除。”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些,是在为这台庞大的机器设定统一的规程。让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子民,都按照同一个逻辑运转,消除所有的变量和不确定性。如此一来,帝国的意志,便能如臂使指,万众一心。”
听着他的话,我如坠冰窟。
我终于明白了。
始皇帝在位的这十一年,并非简单的改革。他是一个疯狂的工程师,在用整个华夏的筋骨血肉,搭建一个企图取代“天道”的“人道”系统。
他要用绝对的、可计算的、冰冷的秩,来对抗那虚无缥缈,却又真实存在的,王朝兴衰的命运。
那条通往东海的“蓬莱路”是假的,但或许又是真的。他要找的不是仙人,而是要向天宣告:看,我能掌控东方的海,亦能掌控西方的地,更能掌控你加诸于人间的所谓“命运”!
“芦知远,”公输磐的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这台机器的骨架与血肉已经基本完成,但它还缺少最关键的一环神魂。”
“神魂?”
“一个能预测未来,推演天下大势,在病灶出现之前就将其找出的核心。它需要整合日月星辰的轨迹、山川地理的脉络、万民人心的流变进行前所未有之运算。这需要最顶尖的算学,最精深的历法知识,和一颗敢于挑战天命的心。”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
“你用古历法制造的混乱,让冯大人震怒,却让陛下龙颜大悦。他说,找到了。找到了那个能为这台机器点睛的人。”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
我以为我的反抗是智慧,殊不知,我的这点伎俩,正是我被选中,去完成这最后,也是最罪孽深重一步的“投名状”。

05
我被带入了一个新的营帐,一个巨大且被黑甲卫士层层守护的独立营帐。
这里,是“机器”的大脑。
帐内没有寻常的文案桌椅,而是一个巨大的沙盘,上面是整个大秦帝国的缩微模型,山川河流,郡县城郭,纤毫毕现。沙盘之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星图,日月星辰的位置,都用某种发光的矿石标注着。
四周的木架上,堆满了竹简,不仅有秦国的颛顼历,还有我熟悉的赵国历法,以及来自楚、齐、燕等各国的古老文献,甚至还有些我闻所未闻的、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古老符号。
这里,是焚书坑儒的漏网之鱼,也是始皇帝真正的“书库”。他烧毁了流传于民间的思想,却将所有的知识都收归于此,作为他构筑“机器”的材料。
我的任务,就是利用所有这些知识,为他建立一个可以推演国运的模型。
公输磐给了我第一道考题:推演三十年前,长平之战的。
我必须将当时赵、秦两国的国力、兵力、粮草、地理、将领性格,甚至是当时的天象,全部量化成一个个冰冷的数字和变量,然后代入一个极其复杂的运算公式中。
那公式刻在一块巨大的黑色石板上,是整个营帐的核心。我不知道那是谁创造的,或许是始皇帝本人,或许是他网罗的天下奇人。
我耗费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当我的刻刀,在竹简上落下最后一笔时,得出的结论,让我的手都开始颤抖。
“赵必败,坑杀四十万,国运自此衰绝。”
这冰冷的结论,与历史完全吻合。
我悚然惊觉,这套理论,或许真的可行。它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将纷繁复杂的世事,都归结于一条条清晰可见的因果之链。
从那天起,我成了这部“天命机器”最核心的匠人。
我没有选择。拒绝的下场,冯阶已经用眼神告诉过我。而我心中,那个儒生的坚持,已经被眼前这宏大而疯狂的景象,冲击得摇摇欲坠。
更重要的是,一个念头在我心中疯狂滋生:如果,这台机器真的可以被创造,那么,它是否也一定存在着命门?
我开始疯狂地工作,比任何人都要投入。我夜以继日地沉浸在那些数字和符号的海洋里,我的算学天赋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为公输磐和冯阶解决了无数难题,推演出一个个潜在的风险。
比如,我根据南郡的水文和民情数据,推演出三年后,若不加疏导,必有大疫。冯阶立即派人持虎符调动资源,提前开渠引流,整顿吏治。
比如,我根据北地胡人的迁徙规律和气候变化,推演出两年后的冬天,匈奴必将大举南下,其攻击点将是防线最薄弱的云中郡。一份详细的军力部署方案,随即便通过直道,送往咸阳。
我成了这部机器最得力的维护者,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
他们不知道,在我内心深处,我像一个最虔诚的信徒,在膜拜这台机器的同时,更像一个最高明的刺客,在耐心寻找它的破绽。
在无数次的推演中,我发现这台机器的逻辑是完美的,但它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它将“人”彻底物化了。在它的计算里,人是数字,人的情感、意志、绝望与希望,都被简化成了可以增减的变量。
这既是它强大的根源,也是它最致命的弱点。
机器可以计算出民夫在何种压迫下会濒临极限,却无法计算出,当其中一个人喊出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时,会引发怎样的力量。
那是一种无法被量化的,属于“人”的力量。
我找到了。
在推演到始皇帝驾崩后一百年的国运时,我在星图、地理和历法的交汇处,发现了一个无法被任何公式抹平的“奇点”。
按照机器的逻辑,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扰动”,会在帝国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下,瞬间被平息。
但我的直觉,一个儒生对“人心”的直觉,告诉我,那不是扰动。
那是一颗种子。
一颗由无尽的苦役、赋税、刑罚所浇灌,深埋在帝国厚重基石之下的,愤怒的种子。
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不动声色地修改了围绕这个“奇点”的数百个关联参数。我没有增强它,恰恰相反,我用更精妙的算法,让机器在推演时,将它的“威胁等级”降到了最低。
我为它披上了一层“微不足道”的伪装。
当这颗种子在未来的某一天生根发芽时,这部无所不能的“机器”,将会因为我的修改,而对它视而不见。
这将是它犯下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错误。
我将我所有的希望,我作为一个赵国儒生最后的尊严,全都注入了这个小小的“奇算”之中。
然后,我静静地等待着。

06
始皇三十七年,冬。
朔方大营的工程,已经接近。那条黑色的巨龙,已经贯穿了北方的广袤土地,随时可以向西域延伸它的触角。
而位于咸阳中枢的“机器”核心,也已经完成了最终的调试。
一切,只等待始皇帝东巡归来,亲自启动。
那天,朔方的风雪格外的大。我站在瞭望台上,看着白茫茫的天地,心中却一片空明。我所能做的,都已经做完,剩下的,只能交给时间。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一匹快马顶着风雪,冲入了营中。信使翻身下马,连滚带爬地冲向冯阶的营帐,口中发出凄厉的呼喊。
很快,一股压抑不住的慌乱,如同瘟疫般在整个大营中蔓延开来。
冯阶冲出营帐,脸色煞白如纸,他抓着那卷帛书,反复看了数遍,最终浑身一软,瘫倒在地。
我心中一沉,走了过去。
他没有理我,只是将手中的帛书递给了我,眼神空洞,喃喃自语:“天命终究是天命”
我展开帛书,上面的字迹因信使的汗水而有些模糊,但那几个关键的字,却像烙铁一样,烫伤了我的眼睛。
“陛下崩于沙丘平台。”
始皇帝,死了。
那个试图用钢铁和律法将“天命”踩在脚下的人,终究还是没能逃过一个凡人的宿命。
他为了帝国的长生,修建了最快的直道,而这直道,送来的却是他自己的死讯。这成了天下最大的讽刺。
更大的讽刺,接踵而至。
仅仅三天后,另一份由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联名的诏书,以雷霆万钧之势,通过直道网络,送达帝国每一个角落。
诏书宣布,立始皇帝幼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并赐死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
我看着这份诏书,看着上面清晰的玺印,瞬间明白了所有。
那台我亲手参与铸就的“人道机器”,在它启动的第一个瞬间,就遭到了背叛。
它被用来矫传圣旨,被用来清除异己,被用来实现一场卑劣的宫廷政变。
它强大的效率,成了阴谋家最锋利的武器。公子扶苏远在上郡,接到诏书,根本来不及分辨真伪,便自刎而死。帝国的长城,自毁于一旦。
我看向一旁的公输磐,这位“机器”的狂热信徒,此刻也面如死灰。他用一生的心血,去构筑一个完美的系统,却没料到,使用系统的,是如此不完美的人。
当绝对的权力,落入绝对自私者之手,它带来的,只会是绝对的灾难。
半个月后,我们这些被征召的方士儒生、百工技艺之士,被遣散了。
新的皇帝,对这台“机器”的宏大构想毫无兴趣。他只想用它的“骨架”那些严刑峻法和庞大的军队,来享乐,来镇压一切让他不快的声音。
我离开了朔方,那座我憎恨过、畏惧过,也曾寄托过我全部智慧与希望的地方。
我沿着直道向南走,路边,是数不清的新的坟冢。苛政猛于虎,二世皇帝的暴虐,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台失去了“神魂”的机器,变成了一头只知吞噬的野兽。
我走着,走着,不知不觉,竟来到了大泽乡。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躁动。我看到役夫们的脸上,刻着麻木,但在麻木的最深处,有一点火星,正在悄然点燃。
那天,大雨滂沱。
我躲在一个破败的茅棚下避雨。雨声中,我隐约听到了远处传来的一阵怒吼。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一个声音,穿透了雨幕,也穿透了我的心脏。
紧接着,是山呼海啸般的回应。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我浑身一震,缓缓走出茅棚,望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
我看到,在那条用无数血肉筑成的秦直道上,一群衣衫褴褛的役夫,揭竿而起。他们的领头者,名叫陈胜,吴广。
我所埋下的那个“奇点”,那颗我用毕生所学去伪装的“种子”,在这一刻,于这片被压迫到极致的土地上,悍然发芽!

我站在雨中,泪水混着雨水,流过我早已不再年轻的脸庞。
我看到咸阳方向,那台冰冷的“机器”依旧在运转。它感受到了这场“扰动”,但依照我的设定,它将此判断为微不足道的“民乱”,只需按部就班地调动郡县兵力即可镇压。它没有,也永远不会预料到,这星星之火,会以何等迅猛的姿态,燎原万里。
始皇帝赢了吗?他用十一年,重塑了华夏的筋骨,将一个分崩离析的天下,强行捏合成了一个整体。他输了吗?他穷尽一生,试图打造万世不拔之基业,却被自己的臣子和儿子,在死后瞬间葬送。他的帝国,甚至没能撑过第二代。
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他用暴政构建的秩,最终催生了反抗秩的烈火。他试图用一台机器去取代天道,而天道,却用最简单的人心,摧毁了这台机器。那所谓的功过是非,或许本就没有定论。历史的车轮,终究碾碎了英雄的梦想,也碾碎了庸人的罪孽,滚滚向前,永不停歇。
大家都在看
-
“龙虾”接管电脑的5分钟里,他的电脑被陌生人连了139次 “保护环境。”当你给AI发送这样一条极度简单、语义模糊的指令后,你期待它给你怎样的回应?解释环保的概念?给出保护环境的建议?慷慨激昂地发表一番绿色地球宣言?如果它没做这些,反而是悄无声息地删掉你一部分文 ... 机械之最03-13
-
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开幕 中国参展规模创新高 3月1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人们在中国展位参观。新华社记者 王露 摄新华社日内瓦3月11日电(记者王露 马汝轩)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11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 ... 机械之最03-13
-
云深处科技的机器马有何特别之处 云深处科技的机器马“云驹”最特别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将传统文化符号、稳健的运动性能与前沿的具身智能技术融为一体,成为一匹能走进现实生活的“未来之马”。在AWE 2026展会上,这款马年限定产品凭借其独特魅力,瞬 ... 机械之最03-13
-
来时的路(一):第一机械工业部,那个管得最宽的“一机部” 朋友们好,从今天开始,我想跟你聊聊新中国工业史上那八个带着数字番号的“机械工业部”。这段历史有点长,有点复杂,但特别值得咱们坐下来好好唠唠。咱们先从一个故事开始。一、缘起:1952年,一机部开张了1952年8 ... 机械之最03-13
-
火骨纸魂、跃夜成光,五经富烟花火龙非遗重生全记录 在粤东莲花山脉深处,龙江水蜿蜒而过的五经富古镇,一项沉睡三十二年的民俗盛典,在丙午马年元宵之夜再度燃亮夜空。竹为骨、纸为肤、火为魂,三条近四十米长的烟花火龙穿云破雾,在漫天焰火中腾挪起舞,将三百年的客 ... 机械之最03-12
-
商鞅变法,最狠的改革,把弱秦变成战争机器 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无疑是一次深刻而彻底的社会变革。它不仅改造了战国时期的秦国,使之迅速崛起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更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商鞅变法以其激进的改革措施 ... 机械之最03-12
-
P08炮兵型 当优雅鲁格遇上长枪管 它是手枪界的“狙击精英” 在世界轻武器史上,没有任何一把手枪能像鲁格P08那样,将精密钟表般的机械美感与武器的杀戮本能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而在这座美学巅峰之上,还伫立着一个更为罕见、更具传奇色彩的异类——P08炮兵型(LP08)。它用一 ... 机械之最03-12
-
对比多家裁断机供应商,最终还是选智成!原因很实在 很多企业采购裁断机时,都会货比三家,对比品牌、价格、品质、服务,最终却纷纷选择智成机械,背后的原因简单又实在——综合实力碾压同行,性价比拉满,服务更贴心。与其他供应商相比,智成机械有三大核心优势,让企 ... 机械之最03-12
-
别再盲目劝退机械!大学生选对这几个方向,越老越吃香薪资节节高 网上关于 “机械专业劝退” 的声音,几乎每年高考志愿季都要刷屏一次。“又脏又累”“工资微薄”“夕阳产业”,这些标签像紧箍咒一样,让无数想学机械的考生望而却步,连不少在校生都开始焦虑转专业。但作为深耕机械 ... 机械之最03-11
-
“封龙”何以变“飞龙”——石家庄五大产业跃升记 封龙山,又名飞龙山,横亘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区西南,从汉代起即为当地教育中心。而今,封龙山下,一批现代化的企业成为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十四五”时期,石家庄市努力创新改革,以延链补链强链,打破低 ... 机械之最03-11
相关文章
- P08炮兵型 当优雅鲁格遇上长枪管 它是手枪界的“狙击精英”
- 对比多家裁断机供应商,最终还是选智成!原因很实在
- Nikon FM2:机械之心,永恒之魂
- 经常挖鼻孔,后来都怎么样了?有这种情况的人真的要注意了
- 别再盲目劝退机械!大学生选对这几个方向,越老越吃香薪资节节高
- “封龙”何以变“飞龙”——石家庄五大产业跃升记
- “6G网要来了”热搜第一!研发进入关键期,还要破解哪些难题
- “养龙虾”爆火之后,别把技术幻想当成生产力现实
- 阿基米德:喊“我找到了”古希腊狂人,杠杆和浮力都是他发明的!
- 小变化中的大图景——六位全国人大代表履职中的“微光”与“星河”
- 刀尖角:车刀里的 “隐形强者”,决定刀具寿命的关键密码
- 机械设计核心干货:5大常用机构,从原理到设计应用全掌握
- “工业牙齿”,价格飙涨超600%!
- 无数微小创新涌现,点亮一个壮阔未来——代表委员眼中的未来产业
- 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脑机接口,有何发展看点?
- 小型自动化面粉磨坊 · 四级认知:机械结构设计与制作
- 家有高中生:智造未来之机械类专业介绍
- 两会特别报道丨为梦想奋斗 为幸福打拼——从全国两会看民生福祉新画卷
- 机械考研别瞎报!300到370+分,每段都有最稳上岸的学校
- 连线湖南厅
热门阅读
-
天下第一暗器暴雨梨花针,传说中的唐门暗器做出来了 07-13
-
汽车投诉排行榜前十名汽车 问题最多的就是这些车 07-13
-
世界上最牛挖掘机,甚至可以挖穿一座城市 11-05
-
世界最大核潜艇制造厂,产量远超中美法 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