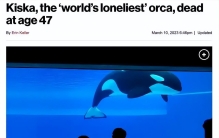世界前4名最臭食物是啥?第一名臭味指数8070!比臭豆腐臭19倍!
那天在朋友家厨房,铝罐在塑料袋里鼓得像小鼓。

他是从北部带回来的,说是“正宗的”,眼里有点孩子般的得意。
我先是以为是笑话,然后看他把罐头放到窗台,掀开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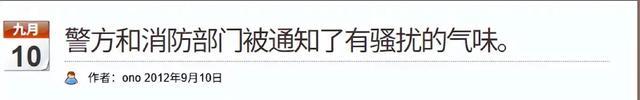
一股像旧下水道混合着把鸡蛋煮熟过头的味道冲出来,
像是从别的时代寄来的气息,把厨房里的空气一刀两断。

后来我才知道,那罐东西叫 surströmming——瑞典的发酵鲱鱼罐头。
有人把它当成世界最难闻的食物来描述,这是个标签,也是一种通行的想象。

小泉武夫等发酵研究者用嗅觉仪器给食物量化后,的确把这类发酵品的臭度列得很靠前。
但味道背后,藏着的是一张很旧的生存地图:北欧的盐价、渔季的短与长、没有冰箱的日子。

16世纪的渔民面对潮涌而来的鲱鱼,手里只有桅杆和一点点盐——盐有时比鱼还值钱。
高盐能保存,但贵;低盐能发酵,但能把鱼变成另一回事,一件能过冬的储备。

把鱼去头保留一小段肠,放进温度不高不低的盐水里,几个月后,厌氧的盐耐细菌做了它们的事。
它们分解脂肪、蛋白,放出硫化氢、丙酸、丁酸、醋酸之类的挥发物。

这些名字听起来学术,但混在一起就是“你闻了会皱眉”的那股味道。
罐子密封后,发酵没停,气体慢慢把罐顶鼓起。

现代罐头通常会高温灭菌,终止微生物活动;surströmming却保留了“活性”,这本身就是把历史和味觉绑在一起的选择。
文化是把味道圈起来的线。

瑞典每年有个传统,第三个八月的星期四,几乎变成了“鲱鱼日”,人们会聚在一起开罐、冲洗、配面包和煮土豆吃。
在北部,这东西像家常菜;在首都和南方,很多人只在节日或是好奇时才碰一碰。

据行业与民间统计,年产量也不是天文数字,吃的人多是本地,出口占比非常低——它并非为了全球化生产的品牌,而是社区记忆的延续。
另一个角度是经济学:当“猎奇消费”席卷网络,视频里有人挑战开罐、有人为了流量拼命下嘴。

这把一种乡土实践送进了全球的娱乐化镜头,让罐头的市场出现短暂的溢价——在一些电商上,一罐能卖到平常罐头好几倍的价钱。
但真正复购的,还是那些把味道和记忆捆绑在一起的人。

法庭、机场和队也曾被这种味道牵着走。
传说里有租客在楼道倒掉罐头汤汁被房东赶走,法庭闻了味道后判房东有理;仓库失火时,爆裂的罐头把恶臭和碎片抛向空中,邻居捂着鼻子撤离。

还有航空公司担心罐头在机舱中继续膨胀导致风险,把它列为禁止携带品。
这些有点荒诞,但正说明了一个事实:当“食品”的物理性影响到公共空间时,规则就会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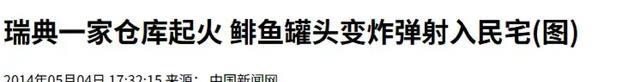
把它和世界上其他“味”并在一张表里比较会很有意思。
格陵兰的 kiviak,把整只小海雀塞进海豹皮里埋了几个月,是因纽特人的冬季补给;

冰岛的 hákarl 用鲨鱼干式发酵;韩国的 hongeo 用鳐鱼发酵,口里会炸开氨气的刺鼻。
这些工艺大多出自同一个逻辑:在寒冷或资源稀缺的环境中,人们用有限的工具延长食物的保存期,同时在有限的选择里发展出风味。

于是所谓“臭”,对外人是禁区,对内部社区却常常是身份的标记。
吃不吃,不只是口味问题,是你要不要把自己放进一个有着共同记忆的群体里。

我认识一些北部的老人,说起开罐的仪式感。
他们会先把鱼冲洗再冲洗,坐在户外,切一点生洋葱,铺开黄油面包,啜一杯小酒。

孩子们会退后几步,看大人怎样把这件“过时的技术”变成宴席的中心。
年轻人当中,有些是出于反叛才吃,有些是出于想象才试,更多人是在社交媒体上次看到它,然后去问长辈这东西是不是传家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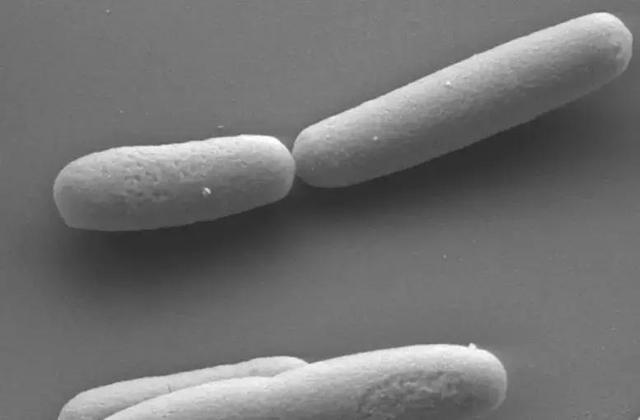
味觉跟记忆勾连得很深。有人把小时候的某个夏天、某次出海和一罐鲱鱼连在一起,那种味道就成了时间的标签。
总有外界把这些食品单纯当作“猎奇道具”来消费,这是另一个时代的惯性。

但在真正的生产地,味道仍是用来维系关系的盐。
有时候,理解一个刺鼻的罐头,比尝过它更重要——你读到的是一个地区的气候、贸易与阶级的残影,是一套用味道记录下来的应对世界的技术。

至于把一罐小小的金盒子放在窗台还是餐桌上,那是每个人的选择。
大家都在看
-
没钱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刑罚,你感受到生活的压力了吗?💔 没钱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刑法。没钱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刑法。你有没有过这种瞬间:想吃一顿好的,看着菜单不敢点;孩子想要一个玩具,只能笑着说下次;父母生病,看着缴费单,连多问一句医生的勇气都没有。很多人说没钱只 ... 世界之最03-06
-
刘结一谈动荡世界中的“中国力量”:最稳定、最可靠、最积极 3月3日,今年全国两会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举行。大会新闻发言人刘结一向中外媒体介绍本次大会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发布会上,除了通报全国政协过去的重点工作与本次政协大 ... 世界之最03-05
-
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在人生的漫漫征途中,我们总在不断追寻,试图抓住那些自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有人痴迷于财富的积累,有人执着于权力的攀升,有人沉醉于名声的远扬。然而,当夜深人静,心灵回归宁静,我们不禁思索: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 世界之最03-05
-
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安全 在全球各类安全评价体系中,冰岛常年稳居世界最安全国家榜首,是公认的和平净土。作为北欧岛国,冰岛人口稀少、社会结构稳定,国家没有正规军队,仅依靠少量警察维护秩序,几乎没有战争与社会动荡风险。极低的犯罪率 ... 世界之最03-05
-
中国发布丨刘结一: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中最稳定、最可靠、最积极的力量 中国网3月3日讯 3月3日,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新闻发言人刘结一表示,中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始终是动荡世界中最稳定、最可靠、最积极的 ... 世界之最03-05
-
英媒罕见承认:这是一次压倒性的胜利,中国站在了世界最前沿 近日,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发布了一则报道,标题本身就带着某种微妙的转折——北京处于一个出人意料的位置:站在可再生能源革命的最前沿。“出人意料”这四个字,暴露了西方媒体长期以来的思维惯性:在他们的叙事里,中 ... 世界之最03-03
-
外国博主狂夸:深圳才是世界最先进城市!看完彻底服了 2025年,海外博主纷纷将中国行列入“打卡”清单,深圳更是成为首选目的地。当你在YouTube搜索关键词“ShenZhen”,不难发现,大量Vlog都以“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为题,定格着这座城市的日常。国外网红深圳行vlog画 ... 世界之最03-03
-
世界排名更新!霍金斯超肖国栋跃居第九,赵心童中国最高准神第一 北京时间2026年3月2日,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排名。特鲁姆普稳居第一,凯伦威尔逊第二,尼尔罗伯逊排名第三位。马克威廉姆斯第四。赵心童排名第五,这意味着他依然是中国排名最高的选手。希金斯第六,塞 ... 世界之最03-02
-
世界上最惨烈的十场战争:凡尔登绞肉机(一场没有赢家的消耗战) 1916年2月21日清晨7时15分,法国东北部默兹河畔的小城凡尔登,天空被炮火撕裂。德军沿着仅6英里长的战线,以每小时十万发的惊人速度倾泻炮弹,密集的爆炸声持续了整整八个小时。一位法国军官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 世界之最03-01
-
中国大桥再添世界之最!广西苍容浔江大桥正式通车 2月28日,随着苍容浔江大桥全线通车,历经近4年建设,广西苍梧至容县高速公路(以下简称“苍容高速”)正式建成通车。苍容高速是广西梧州市与玉林市之间的快速通道,全长约105.31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由中 ... 世界之最03-01
相关文章
- 中国大桥再添世界之最!广西苍容浔江大桥正式通车
- 世界上最惨烈的十场战争:索姆河战役
- 享年55岁世界最老鹦鹉,临终前对主人说了2个字,主人瞬间泪崩
- 世界最聪明的国家:谁是真正的智者
- 美顶级家族最帅“王子”与绝美妻子命丧大海!男才女貌轰动世界
- 宜城,到底骗了多少人?居然拥有5个“世界之最”!
- 广东,到底骗了多少人?居然拥有 10 个 “世界之最”!
- 仪征,到底骗了多少人?居然拥有5个“世界之最”!
- 世界上最亲的人,其实只有两个
- 钟祥,到底骗了多少人?居然拥有5个“世界之最”!
- 中国这8个“世界之最”的景点,去过5个不简单,去7个就太幸福了
- 同样是禁毒,为何中国能被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 带你走进《地理课本》,认识11个“世界之最”
- 成都,到底骗了多少人?居然拥有 10 个 “世界之最”!
- 伊最高领袖:伊朗武器事务“与美国无关”,“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有时也可能遭受沉重打击,以至无法重新站起”
- 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美国白宫守门人背后的那些故事
- 世界上最厉害的人是什么样的?
- 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不是惊天动地,而是“相信”二字
- 千问总裁吴嘉:AI的应用,中国一定会走在世界最前列
- 什么是世界最强最知名
热门阅读
-
世界最恐怖的3个地方,第一名位于中国,你去过吗? 01-04
-
盘点一下世界之最,最长丁丁竟然有60㎝!! 04-26
-
全球最值钱的五大货币,竟然没有人民币和美元 05-10
-
莉娜·安德森 - 世界上最美丽的成人模特 09-25